

房产纠纷:从权利博弈到规则之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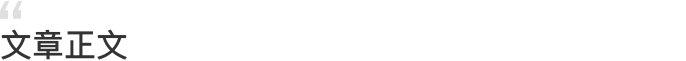

.e08ff51.png)
房产作为中国家庭最重要的资产形式,其价值属性、情感寄托和社会功能的多重性,使得房产纠纷成为民事领域中最为复杂、矛盾最尖锐的类型之一。近年来,随着房价波动、政策调控、权利意识觉醒以及新型交易模式的出现,房产纠纷呈现出数量激增、类型多样、法律关系复杂的特征,对司法实践和社会治理提出了全新挑战。
一、产权确认:房产纠纷的基石之争
房产纠纷的根源多在于产权不清。《民法典》物权编确立了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但历史遗留问题与现行制度的碰撞仍催生大量确权纠纷。
历史遗留房产的确权难题:房改房、集资建房、农村宅基地房屋等因政策演变和手续不全,常出现登记权利人与实际出资人不一致的情况。司法实践逐渐形成“出资+合意”的审查原则,即在无欺诈、胁迫等情况下,实际出资并达成合意建造或购买的一方,即使未登记为权利人,也可能被确认为所有权人。如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判例指出,在家庭内部房产纠纷中,“应综合考虑出资情况、家庭贡献、居住事实等因素,而非单纯依据产权登记”。
借名买房的合同效力与风险:为规避限购政策或获得贷款优惠而产生的借名买房纠纷频发。原则上,借名协议若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如规避限购政策通常被认为损害公共利益),可承认其合同效力,但借名人不能直接取得物权,只能依据合同向出名人主张债权。一旦出名人将房产转让给善意第三人,借名人将面临“钱房两空”的风险。北京、上海等地高院指导意见均强调,借名买房风险自担,借名人应预见并承担政策风险与名人信用风险。
夫妻房产的产权认定:婚前购买、婚后还贷的房产分割是离婚诉讼的焦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规定,此类房产首先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房产归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其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由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补偿数额需综合考虑房产购买价、现价值、还贷情况、婚姻存续年限等因素,计算公式趋于精细化。
二、交易纠纷:过程监管与合同解释的平衡
房产交易环节多、周期长,任一节点的瑕疵都可能引发纠纷,法律在保障交易安全与促进市场效率之间寻求平衡。
“阴阳合同”的效力认定与税务风险:为规避税费而签订价格不同的两份合同(阳合同用于登记,阴合同反映真实交易),司法实践中通常认定反映真实意思的阴合同有效,但当事人可能面临税务机关的追责和处罚。上海某中院判例指出:“以避税为目的签订价格虚低的买卖合同,损害国家税收利益,该价格条款无效,但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
出卖人一房二卖的责任加重:出卖人就同一房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均有效且买受人均要求履行的情况下,法律确定了权利顺位:已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合法占有房屋>合同成立在先>付款情况。这一顺位体现了物权优先于债权、事实状态优先于合同权利的原则。同时,未能取得房产的买受人可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要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惩罚性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贷款失败导致的合同解除:因房贷政策调整或买受人信用变化导致贷款失败,合同是否解除需审查合同约定和当事人过错。如合同约定“贷款不足部分由买受人现金补足”,则买受人不得仅以贷款失败为由解约;如约定“因无法贷款可解除合同”,则买受人需证明已尽合理申请义务。北京高院指导意见强调,应区分政策性调控与个人信用问题,前者可能构成情势变更,双方可协商变更或解除合同。
三、开发与交付:从预售许可到质量保证
商品房预售制度下,购房者在房屋建成前即支付大部分款项,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法律对开发商的义务设定了严格标准。
规划变更的业主同意权:开发商擅自变更小区规划、配套设施(如绿地变车位、承诺的学校消失)是群体性纠纷的常见诱因。法律规定,规划变更需经利害关系业主同意。司法实践对“利害关系”的认定趋于宽松,不仅包括直接受影响的相邻业主,也可能包括因小区整体环境变化而利益受损的全体业主。某典型案例中,开发商将规划中的公共花园改为商业建筑,法院支持了全体业主的诉讼请求,判决恢复原规划。
交付标准与逾期交付的责任:交付条件不仅包括房屋本身的完工,还包括通水、通电、通路等基本使用条件。开发商常以“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表”作为交付条件,但若房屋存在明显质量问题影响基本居住,购房者仍有权拒绝收房。逾期交付的违约金计算,合同约定过低(如每日万分之零点五)可能被法院调整至合理范围。浙江某案例中,法院参照同地段租金标准,将违约金计算标准提高至每日万分之一。
质量缺陷的修复与赔偿:房屋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的,买受人可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一般质量问题的,可要求修复和赔偿损失。对于渗漏、开裂等常见问题,若经多次维修仍未解决,可能被认定为根本违约。近年来,随着精装修房普及,装修标准与质量纠纷激增,法院倾向于审查装修材料的品牌、型号是否与合同约定一致,而非仅仅关注“价格相当”。
四、物业纠纷:从管理到治理的范式转变
物业纠纷反映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下,个人权利与共同利益的冲突,法律理念正从“物业管理”向“社区治理”演进。
业主委员会的诉讼主体资格:业委会能否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曾长期存在争议。《民法典》明确,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可由业委会主张权利。实践中,业委会可就维修资金使用、公共收益分配、物业服务合同等事项提起诉讼。但其权限限于业主大会授权范围,且重大决策(如解聘物业公司)需经法定比例业主同意。
公共收益的归属与公示:电梯广告、外墙广告、公共车位租金等公共收益归全体业主所有。物业公司代为管理的,扣除合理成本后,剩余部分应用于补充维修资金或业主共同决定的其他用途。上海、深圳等地已出现业委会成功诉请物业公司返还数百万公共收益的案例。法院强调,物业公司对公共收益的收支情况负有定期公示义务,不公示或公示不清可能构成违约。
物业服务标准的弹性认定: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标准往往较为笼统(如“提供五星级服务”),纠纷发生时难以直接适用。法院逐渐形成“行业标准+合同约定+实际履行”的综合判断方法。对于安保、保洁、绿化等基础服务,要求达到行业一般水平;对于增值服务,则重点审查合同具体约定。北京某案例中,因小区盗窃案频发,法院认定物业安保存在瑕疵,酌情减免了部分物业费。
五、继承与分割:家庭法视角下的房产处置
房产继承与分割交织着情感、伦理与法律,法院在适用法律规则时往往需兼顾家庭和谐与实质公平。
遗嘱形式要件的严格把握:《民法典》新增打印遗嘱和录像遗嘱形式,但均有严格要件(如打印遗嘱需每页签名并注明年月日;录像遗嘱需记录遗嘱人和见证人肖像及日期)。形式瑕疵可能导致遗嘱无效。某典型案例中,遗嘱人仅在打印遗嘱最后一页签名,未在每页签名,被法院认定无效,房产按法定继承分割。
居住权与所有权的平衡:《民法典》新增居住权制度,为解决“房子归子女,老人无处住”的困境提供了法律工具。居住权可依合同或遗嘱设立,需向登记机构申请登记。居住权人有权占有、使用房屋,但不得转让、继承。这一制度在离婚房产分割、再婚家庭房产安排、以房养老等场景中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如离婚时可将房屋所有权归一方,为另一方设立居住权;老人可将房屋所有权赠与子女,同时为自己设立终身居住权。
农村宅基地房屋的分割限制:宅基地使用权具有身份属性(限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导致非本村成员的配偶或子女在分割时面临障碍。司法实践形成“房地分离”处理原则:房屋作为财产可分割,但宅基地使用权不能由非本村成员单独取得。通常处理方式是,房屋归本村成员一方所有,由其向另一方支付相应补偿款;或双方约定使用方式,待条件成熟时再行分割。
六、新型纠纷:政策调控与商业模式创新的法律回应
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敏感性和商业创新活跃度,催生了诸多新型法律问题。
长租公寓“爆雷”中的资金监管缺位:长租公寓企业利用“租金贷”“高收低租”模式快速扩张,一旦资金链断裂,房东收不到租金欲收回房屋,租客已付租金无处追讨。此类纠纷涉及房东、租客、金融机构、公寓运营商多方主体,法律关系复杂。深圳等地已出台住房租赁资金监管办法,要求租金、押金纳入专用账户监管。司法实践倾向于保护实际居住的租客权益,判决房东在一定期限内不得驱赶租客,同时租客可向公寓运营商追偿损失。
法拍房的权利负担与清场难题:司法拍卖房产数量增加,但法拍房可能隐藏租赁、抵押、欠费等权利负担。法律虽规定“买卖不破租赁”,但针对恶意倒签租赁合同阻挠拍卖的行为,法院可通过审查租赁合同签订时间、租金支付凭证等,认定租赁关系是否真实。对于拒不腾退的被执行人,法院可采取强制清场措施,但过程复杂、周期长,成为影响法拍房成交的主要障碍。
房产中介的“跳单”行为认定:《民法典》首次明确禁止“跳单”,委托人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媒介服务后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的,仍应向中介人支付报酬。但如何界定“同一房源”和“同一中介服务”存在争议。实践中,法院会审查中介是否提供了具体房源信息并促成看房,以及委托人是否利用了该信息与房主直接交易。某典型案例中,买方通过A中介看房后,又通过B中介以更低佣金成交,法院认定构成“跳单”,判令买方支付A中介报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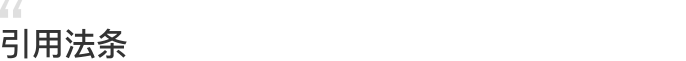



专业定位问题,针对性提供解决方案

























